人类正集体化失去灵性? 四季物候感知钝化敲响文明警钟
昨日立夏,天气却陡然转凉。我们已渐渐忘记了节气,为此深有所感,笔以记之,并赋诗《立夏》一首,聊以述怀。
我们正经历着一场集体性的灵性退化。那些曾经牵动先民心弦的物候变化——第一声布谷鸟啼、第一片梧桐叶落、第一场寒露霜降——在现代人麻木的感官前,已然失去了唤醒生命灵性的魔力。

城市是一座巨大的感官牢笼。恒温的空调房模糊了四季边界,双层玻璃隔绝了风雨气息,人造光源混淆了昼夜更迭。我们的皮肤不再感知春风秋雨,我们的耳膜不再分辨夏蝉秋虫。一位气象学家在报告中写道:"现代人获取天气信息的主要途径是手机软件,而非抬头看天。"这何尝不是一种文明的悲哀?
超市的货架上,四季果蔬常年陈列。草莓在十二月红得刺目,西瓜在一月甜得可疑。我们失去了对"不时不食"的敬畏,也切断了与土地的血脉联系。孩子们以为胡萝卜天生干净整齐,装在塑料袋里;以为牛奶直接来自冰箱,而非温热的乳房。这种认知,正是更为可怕的异化。
更深的危机还在于诗意和审美的荒漠化。古人见落花而伤春,听秋雨而怀远,如今这些细腻的情思,在短视频的轰炸下已成绝响。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记载的"西湖七月半",那种对时令仪式感的执着,在今人看来已是不可理喻的迂阔。我们不再懂得欣赏"小楼一夜听春雨"的意境,我们不再为一片新叶的萌发而感动,不再因一群候鸟的迁徙而沉思。灵性的褪色,使人心变成了坚硬的混凝土,再也泛不起诗意的涟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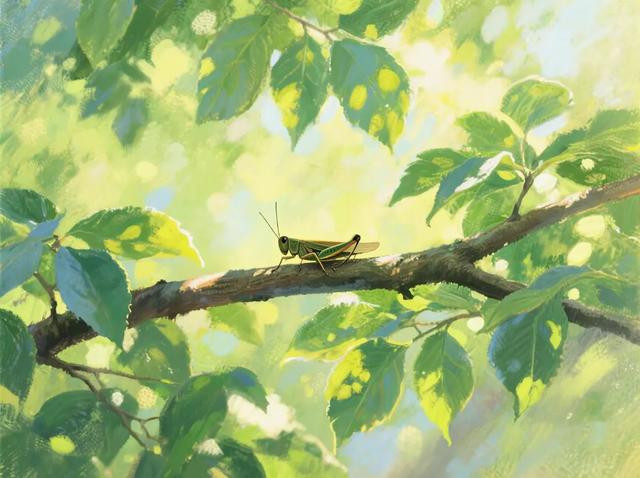
我们似乎不再需要依赖自然的指引来安排生活。然而,这种对四季物候感知的钝化,实际上反映了人类正在集体性地失去一种深层次的灵性——那种与自然和谐共生、敏锐感知生命律动的能力。
曾经,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太阳的升降、月亮的盈亏以及植物的荣枯,制定了二十四节气,以此指导农耕和日常生活。这些智慧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,更是一种与天地万物对话的方式。春天的第一声雷鸣,夏日午后的骤雨,秋天飘落的黄叶,冬夜漫天的雪花,每一个细节都曾被赋予意义,成为人们内心情感的一部分。然而,在今天,许多人甚至连“春分”、“秋分”这样的基本节气名称也记不全,更遑论从中体会到自然的启示。
当人们不再关注外界的变化时,内心就会逐渐封闭。比利时作家梅·萨藤曾说:“如果一个人专心致志地瞧一朵花,一块石头,一棵树,这时启迪性的事物便会发生。”但如今,还有多少人愿意停下脚步,认真凝视一朵花的绽放?又有多少人能够从一片落叶中读出时间的流逝?我们忙于追逐效率与利益,却忽略了生命这个最本真的存在。
灵性并非宗教意义上的超自然力量,而是一种对世界的敏感度和共情能力。它要求我们打开感官,去倾听风的声音,触摸雨的温度,感受阳光洒在皮肤上的温暖。只有当我们重新建立起与大自然的联系,才能找回那份久违的平静与满足。

自然从未停止诉说,只是人类渐渐忘了如何去听。因此,重拾对四季物候的感知,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,更是对个体灵性的唤醒。让我们尝试放慢脚步,走出高楼大厦的阴影,去拥抱大自然的怀抱。
或许某一天清晨,你也会像川端康成那样,在寂静中发现海棠花未眠的美好,并为之感动唏嘘。
或许该重拾一些古老的智慧:在阳台上种一盆会枯萎的花,在周末走进一片真实的树林,让孩子用手掌而非屏幕去触摸这个世界。重获对四季的触感,就是找回我们作为人的温度与灵性。

▶七绝·立夏 原创 许子枋
风前犹自怯衣单,红瘦绿肥不忍看。
却喜夭桃皆挂果,荼蘼架底倚阑干。
▶红瘦绿肥间的时光触感——读《七绝·立夏》
这首七绝以立夏为坐标,在花谢果生的自然更迭中,铺展开一幅暗含生命哲理的季节图卷。诗人以敏锐的物候触角,捕捉到夏初特有的矛盾美感,在二十八字间完成了一场对时光的细腻解构。
全诗结构暗合古典诗歌"起承转合"的黄金律。起句"风前犹自怯衣单"以触觉破题,凉风掠过单衣的微妙触感,既点明乍暖还寒的节候特征,又暗示着诗人面对季节转换时的心理震颤。承句"红瘦绿肥不忍看"将视角转向视觉,李清照"绿肥红瘦"的典故在此被翻转重组,"不忍"二字透露出对春逝的无限怅惘。转句"却喜夭桃皆挂果"笔锋陡转,在花谢的怅惘中窥见果实新生的喜悦,形成情感上的巨大张力。合句"荼蘼架底倚阑干"以动态画面收束全篇,荼蘼作为春末最后的花信,其架下独倚的身影将惜春与迎夏的双重情愫凝结为永恒的瞬间。

诗中物象的选取极具深意。"红瘦绿肥"不仅是色彩与形态的对比,更暗喻着生命形态的转化规律。夭桃挂果的意象,将植物的生命周期具象为可视的审美对象,使时间流逝获得了物质性的呈现。荼蘼架与阑干的组合,构建出纵深的空间感,诗人倚栏的姿态仿佛站在季节的门槛上,回望春光的背影,凝望夏日的面容。
这种对时光的辩证认知,使诗歌跳出了伤春悲秋的传统框架。凉风中的衣单之怯与果实初结的欣喜,花事阑珊的不忍与荼蘼独倚的从容,共同编织成复杂而真实的情感网络。诗人不是简单地咏叹春归,而是在季节嬗变中领悟到生命循环的永恒韵律——每个终点都孕育着新的起点,正如荼蘼谢尽处,正是绿荫渐浓时。
结尾的倚栏身影,定格成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凭栏意象。这个动作既是对流逝时光的目送,也是对新生希望的守望,在方寸栏杆之间,完成了对永恒刹那的诗意捕捉。当夏日的风掠过荼蘼架,吹动诗人的衣袂,我们仿佛听见时光在红瘦绿肥间流淌的潺潺水声。
